
学中医,不是一朝一夕的事,也不是只看几本教材、背几句《黄帝内经》就能学明白的。中医自古传承有序,尤其唐宋以降,到了金元一代,更是名医辈出、学说并兴。如果想学得好,不能不读古人,更不能不懂古人。那些留下经典著作的人,不光是会看病,更有独到的见解和鲜明的风格。从唐代的孙思邈、王焘,到金元的李杲、刘完素、张从正、朱震亨,每一个人的医学思想,放到今天都还有不少可借鉴的地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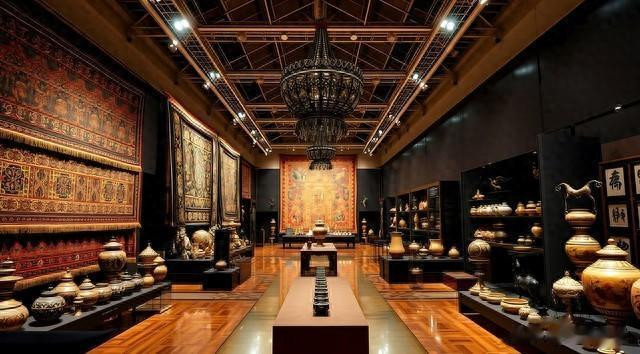
先看唐代的孙思邈,人称“药王”,在太白山隐居几十年,写出《千金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共六十卷,后来整理为九十三卷。这两部书内容虽然有些地方不够精炼,有浮泛重复之嫌,但其中的用意和用药方法,确实独具匠心,体现了一个大家的水平。《千金》之名,也不是虚夸,说的是一方可值千金,关键时刻能救命。唐代还有王焘写的《外台秘要》,这本书收录了大量秘传方,门类分明,结构清晰,被后人称作医书的类典。这两部书,一个重实用,一个重归类,都为后世留下了很好的范本。
到了金元时期,中医理论进一步细化,各立门户,形成了鲜明的学术风格。李杲,人称东垣老人,非常强调脾胃。他认为“后天之本”在脾胃,气血生化全靠这两个脏腑运作顺畅。他的《脾胃论》《辨惑论》《兰室秘藏》被后人整理为《东垣十书》,一再流传。李杲用药讲究升清、温燥,经常用到补中益气汤、升阳散火汤等方子,药材中常见苍术、白术、葛根、陈皮、羌活这些。用药风格上有人说他像韩信带兵——多多益善,当然,这种繁复用药也容易出现偏杂,但他的立意明确,始终围绕脾胃,这就是他的“家法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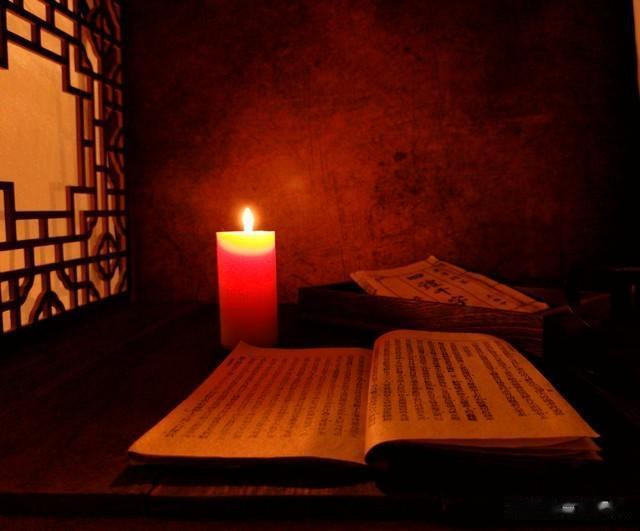
与李杲不同,刘完素主张“火热致病”,重在“寒凉清热”。他的火学理论源于《内经》,但也有很多自己的发挥。他把病因归为火之虚实、火之升降、火之潜伏,有时说得太玄,但也有实际应用价值。像他提出的六一散、防风通圣散,都是能“奇而不悖正”的好方。虽然他的理论难以尽通《内经》之旨,但在治疗热性病、实火证等方面,确实独具一格。
再看朱丹溪,主张“阳常有余,阴常不足”,提出“阴虚是百病之源”,他强调滋阴,却不盲目补阳。他的《丹溪心法》对各种杂病的分析很精妙,总结出“气、血、痰、郁”四字决,认为大多数杂病都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入手。气证用四君子汤,血证用四物汤,痰证用二陈汤,郁证用越鞠丸,灵活搭配,药简而效专。他的观点和其他几位相比,更重整体调理,对今天的慢性病、情志病都有启发。
再说张从正,也就是张子和,与前三位不同,他的主张是“攻邪为先”,喜欢用猛药驱邪,比如大黄、芒硝、牵牛子、甘遂这些,都是泻下峻剂。他认为病邪不去,正气难安,这种思路适合急症实证。只不过他也强调“中病即止”,攻得太猛,元气受损,就不好收场了。子和之法,是对那种拖泥带水、动不动就养补的中医思路的纠偏,适合“重病重药”,但也要分清寒热虚实,不能乱用。

这几位金元大家,被称为“金元四大家”,各有主张,各有成就。刘完素重火、张子和主攻、李东垣扶脾、朱丹溪补阴,四家合观,几乎涵盖了中医治疗的主流思路。学中医若能读懂他们,就等于打开了一把钥匙,不至于看病时只会套方、机械对号。重要的是,不能只看他们留下的方子,还要明白他们是怎么想的、为什么这样用药,这样才能学得活、用得准。
学中医是一条漫长的路,但也是一条越走越宽的路。古人留下的不光是书本,更是思路和方法。跟着这些真正懂病、懂药的医家走,才不至于在纷繁复杂的病症中迷路。今天想把中医学好,不如先从这四大家的书入手,不急着求多,先读透几部,体会得深了,用药自然也就稳了。中医不怕慢学,就怕学得浅。把根扎深了,将来不管风吹雨打,都能立得住。
泰禾优配-股市开户网上开户流程-股票配资首选门户网站-南宁股票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